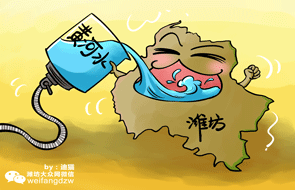“千里漫行话潍坊”安丘行有感----青云寺
2017-11-02 15:13:00 来源:大众网 我要评论
关键词:
[提要]“虔诚烧香何必远去南海,真心拜佛此地即是西天”这是青云寺门口的楹对。这座美丽的寺庙安静地坐落在安丘山峦环抱着的半山腰,静得我这个游人之前几乎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提要]“虔诚烧香何必远去南海,真心拜佛此地即是西天”这是青云寺门口的楹对。这座美丽的寺庙安静地坐落在安丘山峦环抱着的半山腰,静得我这个游人之前几乎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虔诚烧香何必远去南海,真心拜佛此地即是西天
“虔诚烧香何必远去南海,真心拜佛此地即是西天”这是青云寺门口的楹对。这座美丽的寺庙安静地坐落在安丘山峦环抱着的半山腰,静得我这个游人之前几乎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原本,是看银杏树去的。相传由孔子来走访女婿公冶长当年读书的地方而在此种下的两棵银杏树同样坐落在这半山腰。还在对面远山的路上,就已经能望见这边山间的一些明黄已经开始耀眼。秋还未深,若是过两个星期,怕是半座山都要被染成金色。
树是极好的,再高百级台阶的公冶长读书之院也是极好的,恰如预期。而意料之外的,是这青云寺。
或许在山东这地方,儒家的影响力还是大些,祈求高考得中的人比寻求内心平静的人更多;又或许是因为建于唐代的寺院毕竟不如距今两千多年的孔子及其弟子历史久远----如此灿烂的名胜集中于一处,公冶长书院和古银杏树的名头似乎大过(甚至大大压过)了这座绿云掩映中的寺庙。但这“不出名”中的心平气合、稳稳当当却也正是它身为修身养性之地,值得向往宁静者真心喜爱的特质。
叫“青云”的寺庙不少,浙江、辽宁、吉林、山西都有,甚至同在山东省内的淄博市也有一座同名。但这不妨碍。同名同姓的人更多,叫“静”的,不一定文静;叫“壮”的,不一定壮硕。而这座青云寺,名副其实。
依山而建的寺庙,远而望之,不仅所处之地绿树如云环绕其间,又有两棵著名古树相伴而邻;从寺庙往外远眺,远山黛影,在北方少见的层层梯田绿得深深浅浅。最难得的是寺院的修建和维护,彻底与自然融为一体----高大的楸树如同挺拔的天将,用山林原本的样子守护着神灵的殿堂;通往大殿的石阶上,两株大树伸展而出,不论是先有树还是先有阶,修建的人都给自然留了余地、驻守在此的人给生长留了空间。
最感人的,莫过于此。
佛说,相由心生。如今的一切,都是过去一切的呈现。
选了这样一块挖口井都五百年水位不减的宝地,先人是有心的;曾经的影壁连同上面已死的小枫树都能保留,再建者是有心的;从哼哈二将的神态到梁柱墙瓦的花纹颜色,每一个再次描绘的工匠都用了心。佛家地,最能打动世人的,便是用心二字;在浮躁的时代和社会,这两个字尤为珍贵。
同时,青云寺也是沉得住气的。山路,依然弯弯曲曲;没有售卖的小贩、没有我们已经见习惯了的商业气息,甚至没有让取舍皆难的高昂门票和名贵香火钱。门前平坦的场地,是未经水泥、大理石覆盖的小石子,走在上面,鞋底与石子、石子与石子间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在山间不至多到喧闹的游人声、时常鸣起鸟叫声衬托下,让人感觉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风过树叶沙沙响,掉落的银杏果,飘落的树叶,为石子地和人心,配上点点颜色。
想想多少年没这样闲适地走石子路了?覆盖上水泥、地砖、大理石的街道和广场,光滑坚硬,或者富贵大气,但也隔绝了我们与大地的亲近。记忆中的脚步,是高跟鞋的踢踢踏踏,还是光溜溜地面上的打滑?什么样的街道,我们花重金请了保洁员、采购了扫地车,依然污秽与废弃物屡见不鲜?而这里,没有垃圾。落叶与踩碎的果泥是景色的一部分,两个80年代的垃圾箱、两个藤编的箩筐,就影响了人们所有的自觉。
我不反对高楼大厦、我也享受繁华中的便利,我只是很喜欢,在佛家之地,在世人不远处,还有这样一方小寺,从开始到现在,容颜不曾老去,同时又保留了最初的心。
我不信佛,但我信人。我相信世间的人,有好的、有善念。
见过了太多香火鼎盛、人们络绎不绝的名川圣殿,听过了太多为名为利不择手段的俗人甚至佛家子弟,当莲花池中堆了满满的硬币、当放生池里乌龟多无法生存彼此厮杀成炼狱、当警察不得不来门口维持排队消防车来灭烟消火……若你也曾有过相同的体会,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几乎为这青云寺落泪。
在这里,大门旁,两只小猫依偎着晒太阳,有人走进时一只警觉地躲进破了一格的纸窗,是灵兽该有的状态;在这里,碑石后面种的菜、台阶上晒着的大红薯,如此可爱;在这里,访客散去时,与我们交谈过的僧人在自己禅房前坐下,抚摸地上的黄狗,它幸福地眯了眼抬起头……那一刻,我看见了人性的光。
善良,是不刻意表现时的行动;佛法,是平凡世界中,与众生相处,也依然坚持的信念。若有再访,希望它仍然是现在的模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虔诚烧香何必远去南海,真心拜佛此地即是西天”这是青云寺门口的楹对。这座美丽的寺庙安静地坐落在安丘山峦环抱着的半山腰,静得我这个游人之前几乎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原本,是看银杏树去的。相传由孔子来走访女婿公冶长当年读书的地方而在此种下的两棵银杏树同样坐落在这半山腰。还在对面远山的路上,就已经能望见这边山间的一些明黄已经开始耀眼。秋还未深,若是过两个星期,怕是半座山都要被染成金色。
树是极好的,再高百级台阶的公冶长读书之院也是极好的,恰如预期。而意料之外的,是这青云寺。
或许在山东这地方,儒家的影响力还是大些,祈求高考得中的人比寻求内心平静的人更多;又或许是因为建于唐代的寺院毕竟不如距今两千多年的孔子及其弟子历史久远----如此灿烂的名胜集中于一处,公冶长书院和古银杏树的名头似乎大过(甚至大大压过)了这座绿云掩映中的寺庙。但这“不出名”中的心平气合、稳稳当当却也正是它身为修身养性之地,值得向往宁静者真心喜爱的特质。
叫“青云”的寺庙不少,浙江、辽宁、吉林、山西都有,甚至同在山东省内的淄博市也有一座同名。但这不妨碍。同名同姓的人更多,叫“静”的,不一定文静;叫“壮”的,不一定壮硕。而这座青云寺,名副其实。
依山而建的寺庙,远而望之,不仅所处之地绿树如云环绕其间,又有两棵著名古树相伴而邻;从寺庙往外远眺,远山黛影,在北方少见的层层梯田绿得深深浅浅。最难得的是寺院的修建和维护,彻底与自然融为一体----高大的楸树如同挺拔的天将,用山林原本的样子守护着神灵的殿堂;通往大殿的石阶上,两株大树伸展而出,不论是先有树还是先有阶,修建的人都给自然留了余地、驻守在此的人给生长留了空间。
最感人的,莫过于此。
佛说,相由心生。如今的一切,都是过去一切的呈现。
选了这样一块挖口井都五百年水位不减的宝地,先人是有心的;曾经的影壁连同上面已死的小枫树都能保留,再建者是有心的;从哼哈二将的神态到梁柱墙瓦的花纹颜色,每一个再次描绘的工匠都用了心。佛家地,最能打动世人的,便是用心二字;在浮躁的时代和社会,这两个字尤为珍贵。
同时,青云寺也是沉得住气的。山路,依然弯弯曲曲;没有售卖的小贩、没有我们已经见习惯了的商业气息,甚至没有让取舍皆难的高昂门票和名贵香火钱。门前平坦的场地,是未经水泥、大理石覆盖的小石子,走在上面,鞋底与石子、石子与石子间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在山间不至多到喧闹的游人声、时常鸣起鸟叫声衬托下,让人感觉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风过树叶沙沙响,掉落的银杏果,飘落的树叶,为石子地和人心,配上点点颜色。
想想多少年没这样闲适地走石子路了?覆盖上水泥、地砖、大理石的街道和广场,光滑坚硬,或者富贵大气,但也隔绝了我们与大地的亲近。记忆中的脚步,是高跟鞋的踢踢踏踏,还是光溜溜地面上的打滑?什么样的街道,我们花重金请了保洁员、采购了扫地车,依然污秽与废弃物屡见不鲜?而这里,没有垃圾。落叶与踩碎的果泥是景色的一部分,两个80年代的垃圾箱、两个藤编的箩筐,就影响了人们所有的自觉。
我不反对高楼大厦、我也享受繁华中的便利,我只是很喜欢,在佛家之地,在世人不远处,还有这样一方小寺,从开始到现在,容颜不曾老去,同时又保留了最初的心。
我不信佛,但我信人。我相信世间的人,有好的、有善念。
见过了太多香火鼎盛、人们络绎不绝的名川圣殿,听过了太多为名为利不择手段的俗人甚至佛家子弟,当莲花池中堆了满满的硬币、当放生池里乌龟多无法生存彼此厮杀成炼狱、当警察不得不来门口维持排队消防车来灭烟消火……若你也曾有过相同的体会,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几乎为这青云寺落泪。
在这里,大门旁,两只小猫依偎着晒太阳,有人走进时一只警觉地躲进破了一格的纸窗,是灵兽该有的状态;在这里,碑石后面种的菜、台阶上晒着的大红薯,如此可爱;在这里,访客散去时,与我们交谈过的僧人在自己禅房前坐下,抚摸地上的黄狗,它幸福地眯了眼抬起头……那一刻,我看见了人性的光。
善良,是不刻意表现时的行动;佛法,是平凡世界中,与众生相处,也依然坚持的信念。若有再访,希望它仍然是现在的模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
向本网爆料,请拨打热线电话:0536-8797878,或登录潍坊大众网官方微博(@潍坊大众网)、潍坊大众网官方微信(微信号:weifangdzw)。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焦雪
责任编辑:焦雪
相关新闻推荐:
- 千里漫行话潍坊 走进公冶长书院2017-11-02 14:07:00
- 千里漫行话潍坊——走进安丘2017-11-02 11:23:00
- 小城旧(酒)事2017-11-02 11:09:00
- 为幼儿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2017-10-23 10:54:00
我要提供新闻线索(一旦采用,奖励最少20元话费,所有内容均为您保密)
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
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