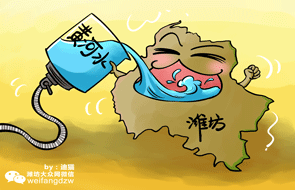俺庄有棵老槐树,从岁数上讲,当属一个老寿星。
老槐树与俺庄同龄,活了八百多年了,身子骨依然很健壮,像是一轮夕阳,一如既往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常年为村里人造福不止。
夏日,老槐树一天到晚擎着一把大绿伞,既为在此歇息的人们遮阳乘凉,还帮助人们吸收二氧化碳,制氧输氧,营造环保氛围。
在我儿时的心目中,老槐树更像一位亲切和蔼、与人为善的老爷爷。
老槐树的躯干有两丈多高,粗大的腹部像是动过一次大手术,一道又宽又深的大疤裂痕,藏进一个小孩绰绰有余。
老槐树裸露在外的生命之根像是粗大的龙爪,在沧桑岁月冲刷之下,有一段变得光滑洁净,这倒成了玩童的天然游乐设施,孩子们像在老爷爷面前撒娇,时而用手触摸着耍,时而当作木凳子坐着玩,高兴了,甚至还当踏板练习立定跳远呢。
记得爷爷和奶奶都曾经说过:“老槐树长得旺,全村人就吉祥”。在很多老人看来,这棵老槐树像是一位保佑人们吉祥如意的老菩萨。只要老槐树枝叶茂盛,就能给全村父老带来幸福和安康。
正因为从小就深受这种理念的熏陶,使得我对老槐树的情感越来越深,深得一点不比村前那条河和庄后那片果园浅。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村里常在老槐树附近搭戏台,放电影,因为这里不仅离村近,而且平坦,开阔,搁人多。最重要的,是借助大槐树的美好形象,赋予本村文化活动更多的精彩与内涵。
儿时的我们,只要晚上在老槐树这里唱戏或者放电影,总是顾不上吃晚饭,太阳老高就来抢占地盘,有凳子的放上凳子,没凳子的就用石块和砖头占地方,一个孩子占一大片,至少足够一家人坐的。
开演以后,有些顽皮好动的孩子,凭着座位不坐,偏偏爬到老槐树的枝杈上,就像骑在自己爷爷的脖子上撒娇,两条腿叉开,不停地前后左右摆动着,看上去,得意得有些忘形。
不过,呆不了多长时间,一旦被家里人或者被爱管闲事的长辈看见,坐在树杈上的孩子,就会被严厉吆喝下来,有时还会被训斥和臭骂一顿。小孩子记性短,下次有机会,还是照爬不误。
一九六一年,一股神兮兮的迷信之风吹到了这棵老槐树上,使得老槐树一夜之间成了仙。一传十,十传百,不光俺庄,连周围好多村子的人都纷纷前来,先往树上拴红布条,然后跪在树下祈祷。有的老太太还摆上供品、烧着香火求事许愿。一时间,老槐树成了一座庙,一尊佛。
事实上,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将老槐树神化,顶多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愿望而已。半年以后,随着祈求跪拜屡屡无效,神化老槐树的虚无之风自行消失,质朴厚道的老槐树,又恢复了它往日的正常生活。
后来,我和老槐树都被拔了出来。不同的是,我是因工作需要被移植到钢筋水泥浇筑的县城公仆楼房里,还活着,而且活得还算自在,因为我一日三餐手里有个铁饭碗,吃喝无忧。
老槐树就没有我幸运了,就那么一霎,就变成了村庄规划的牺牲品。老当益壮的身躯被钢锯肢解卖掉,枝叶则被填进了烧火做饭的锅灶底下。
失去了老槐树,村里好多人的内心感受,都比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还难过。我,虽说常年在外,但对老槐树的敬仰和念想程度,丝毫不亚于一直生活在村里的那些人。
每次回老家,我总忘不了到老槐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上几眼,甜蜜的回忆与苦涩的感受,搅合在一起,说不出是啥滋味。反正不好受,心里难过得很。
无能为力的我,要想再与老槐树亲切会晤和牵手,唯有到梦境去,才能找回昔日那种其乐融融的美好感觉。
在先辈的言传里,俺家的老根,就扎在山西洪洞县那棵老槐树底下。我常遐想,尚若这棵老槐树在天有灵,说不定又随风飘回山西老家那地方认祖归宗去了。
或许,这是老槐树唯一可取的一个选择。
因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上苍立下的自然定律,谁都不能也无力抗拒和改变。